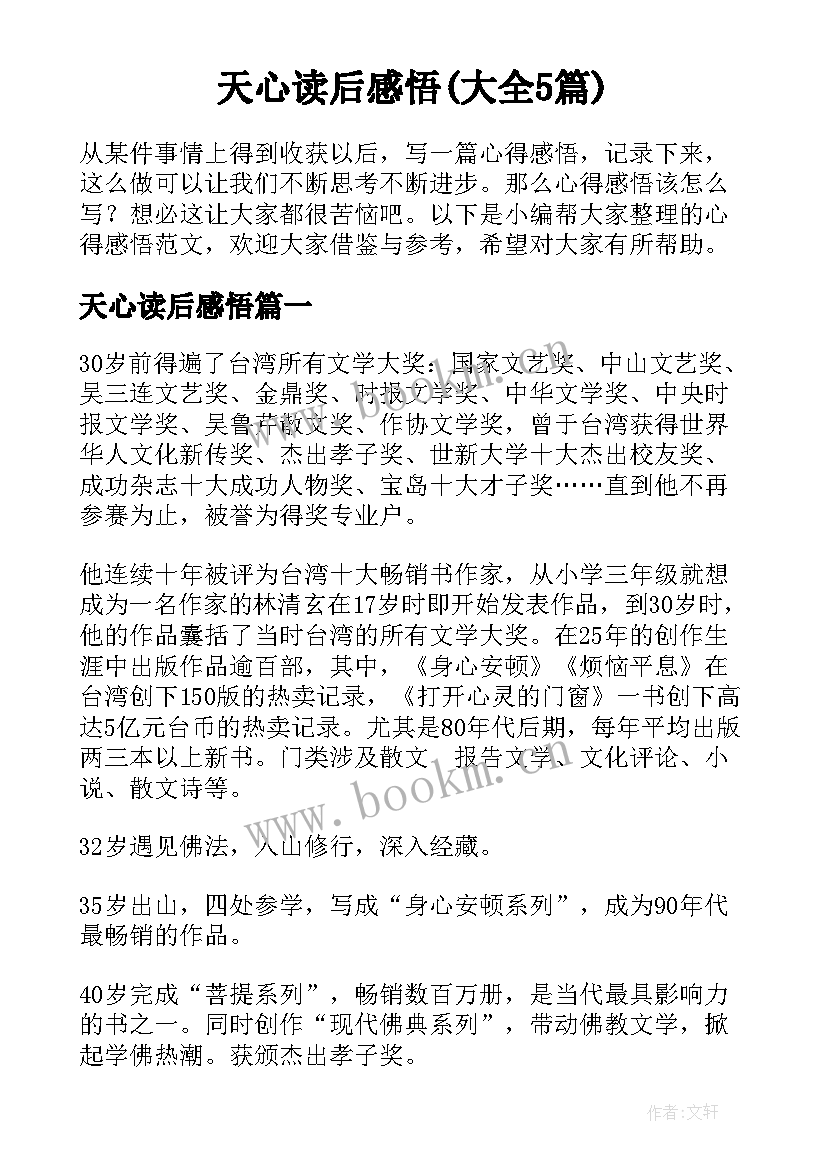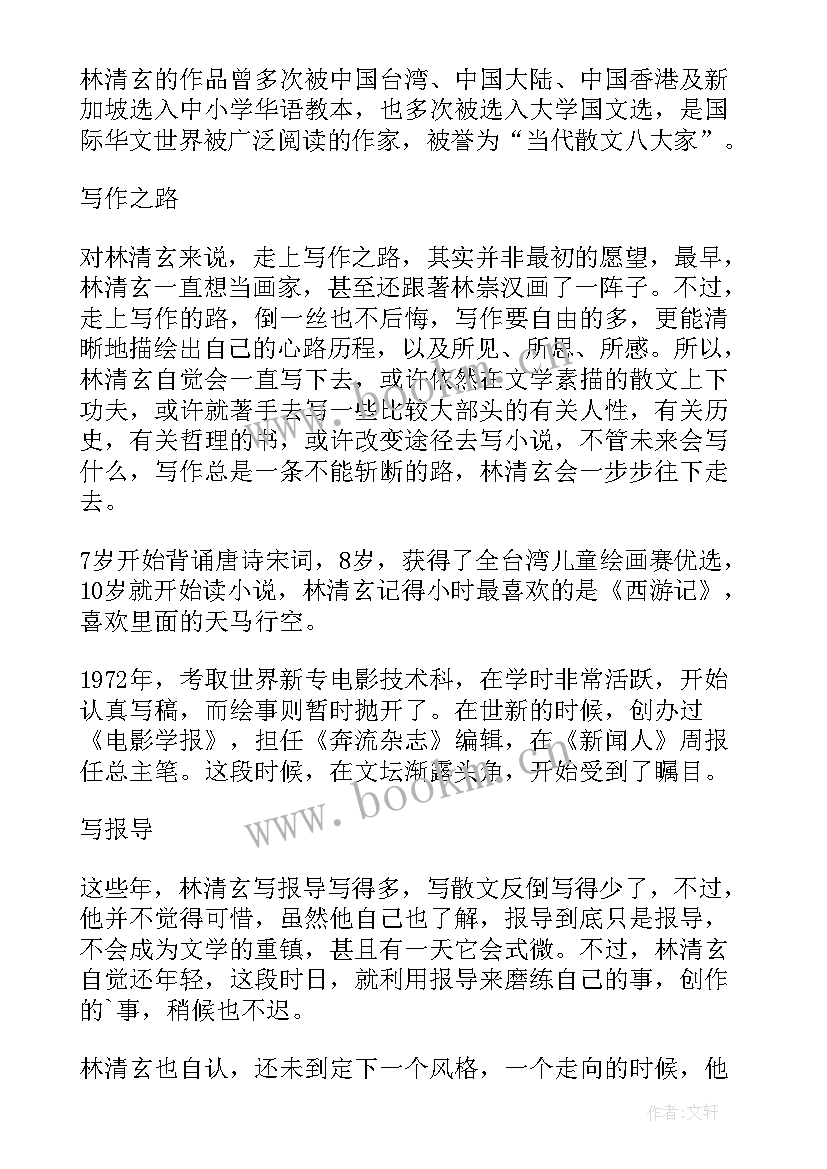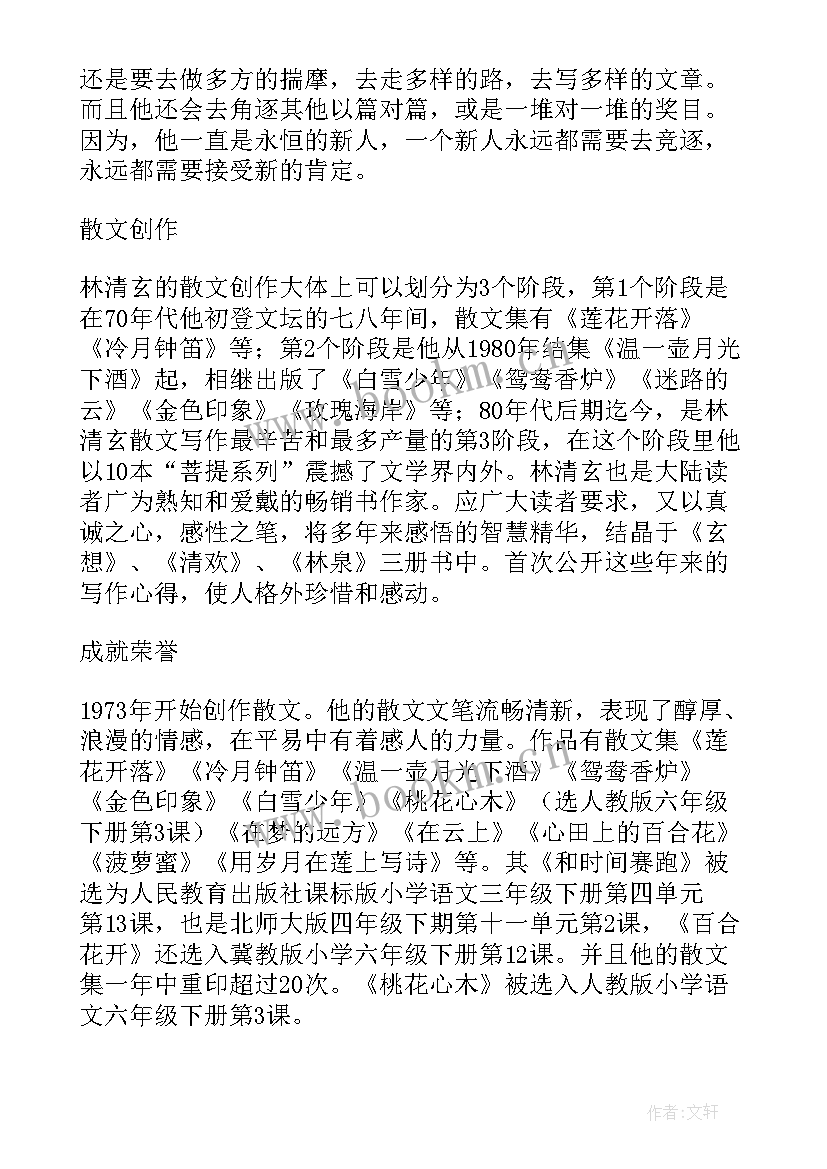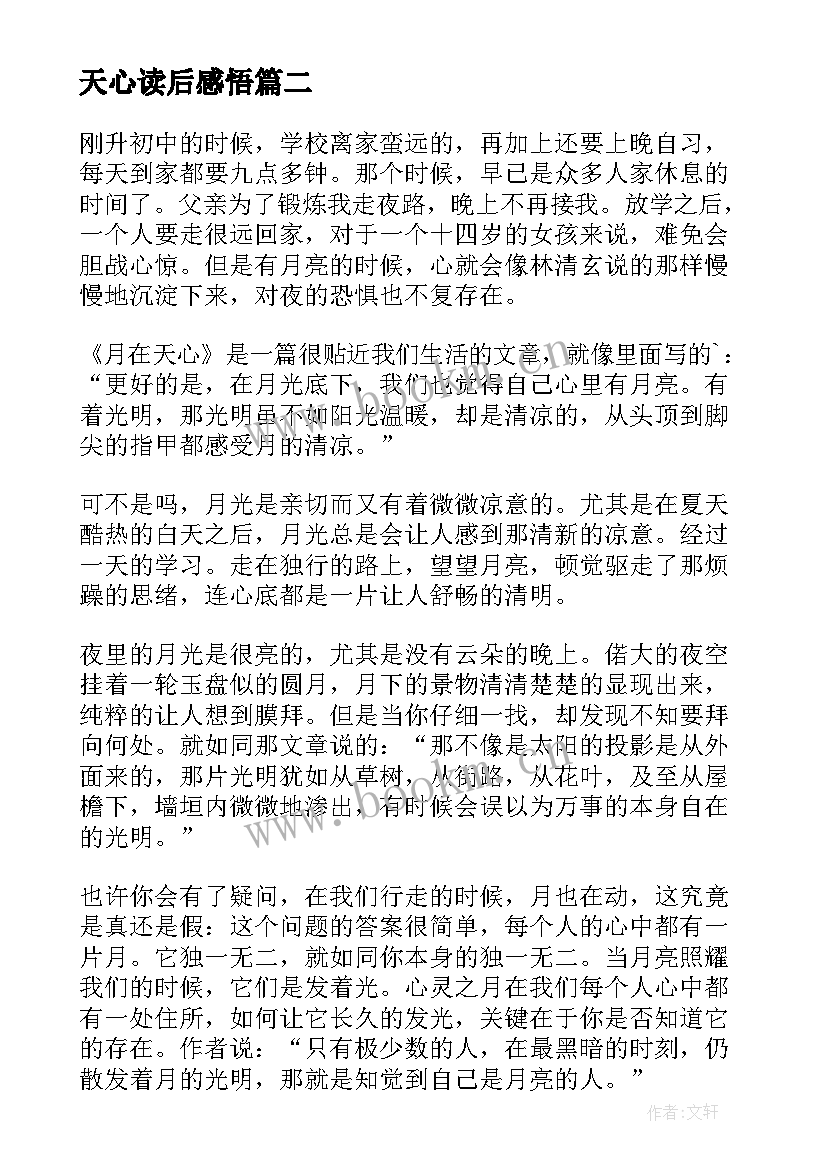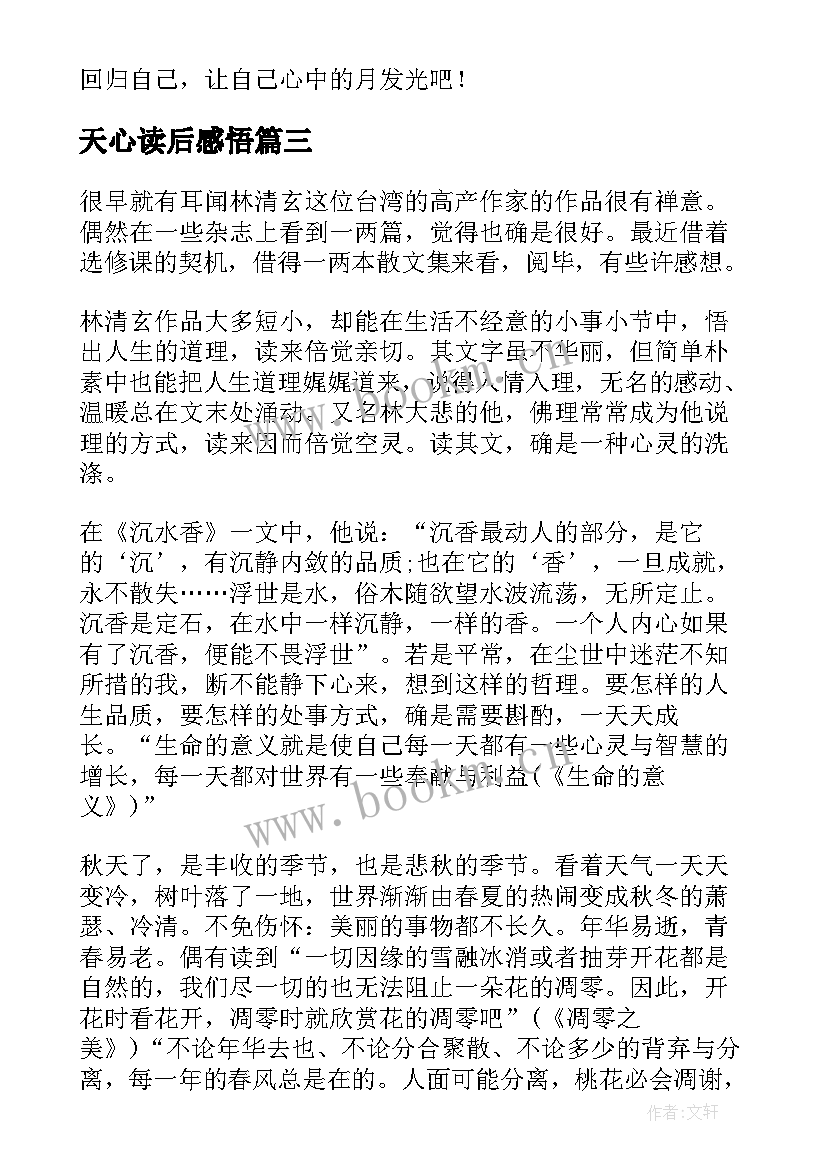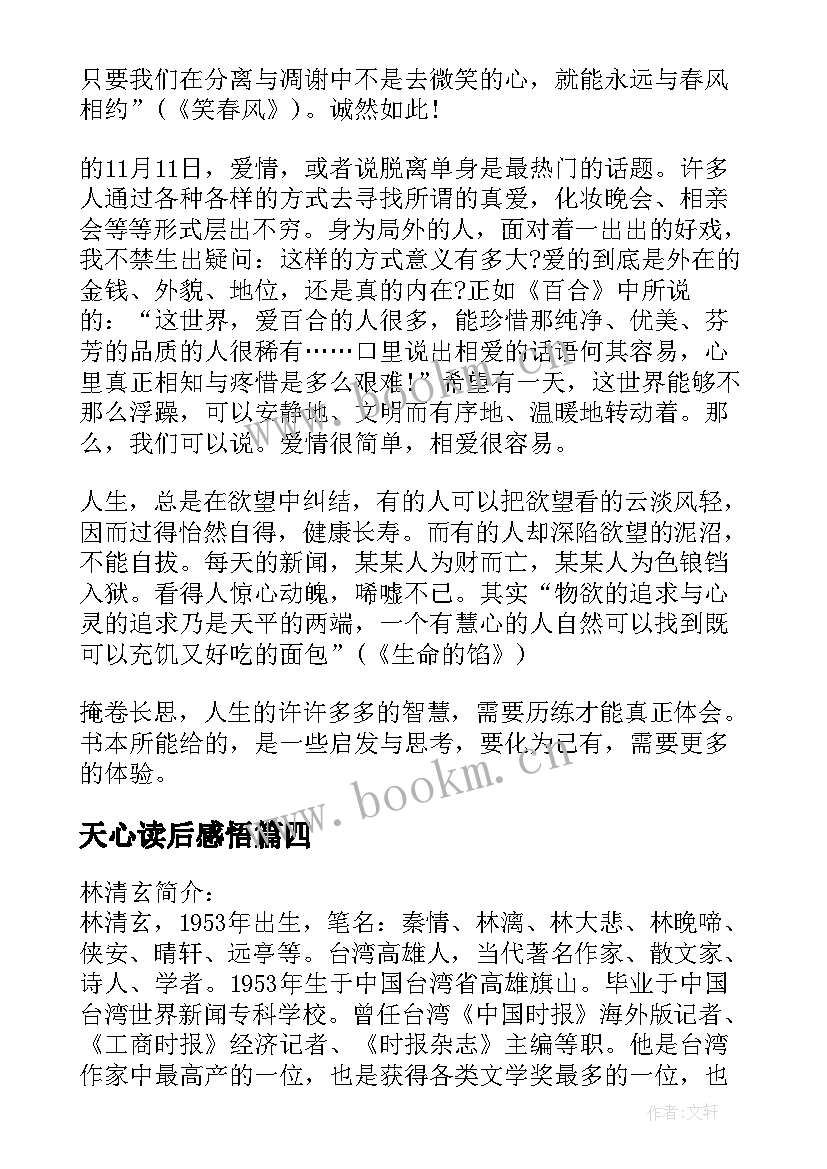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,写一篇心得感悟,记录下来,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。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?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。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,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天心读后感悟篇一
30岁前得遍了台湾所有文学大奖:国家文艺奖、中山文艺奖、吴三连文艺奖、金鼎奖、时报文学奖、中华文学奖、中央时报文学奖、吴鲁芹散文奖、作协文学奖,曾于台湾获得世界华人文化新传奖、杰出孝子奖、世新大学十大杰出校友奖、成功杂志十大成功人物奖、宝岛十大才子奖……直到他不再参赛为止,被誉为得奖专业户。
他连续十年被评为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,从小学三年级就想成为一名作家的林清玄在17岁时即开始发表作品,到30岁时,他的作品囊括了当时台湾的所有文学大奖。在25年的创作生涯中出版作品逾百部,其中,《身心安顿》《烦恼平息》在台湾创下150版的热卖记录,《打开心灵的门窗》一书创下高达5亿元台币的热卖记录。尤其是80年代后期,每年平均出版两三本以上新书。门类涉及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文化评论、小说、散文诗等。
32岁遇见佛法,入山修行,深入经藏。
35岁出山,四处参学,写成“身心安顿系列”,成为90年代最畅销的作品。
40岁完成“菩提系列”,畅销数百万册,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书之一。同时创作“现代佛典系列”,带动佛教文学,掀起学佛热潮。获颁杰出孝子奖。
林清玄的作品曾多次被中国台湾、中国大陆、中国香港及新加坡选入中小学华语教本,也多次被选入大学国文选,是国际华文世界被广泛阅读的作家,被誉为“当代散文八大家”。
写作之路
对林清玄来说,走上写作之路,其实并非最初的愿望,最早,林清玄一直想当画家,甚至还跟著林崇汉画了一阵子。不过,走上写作的路,倒一丝也不后悔,写作要自由的多,更能清晰地描绘出自己的心路历程,以及所见、所思、所感。所以,林清玄自觉会一直写下去,或许依然在文学素描的散文上下功夫,或许就著手去写一些比较大部头的有关人性,有关历史,有关哲理的书,或许改变途径去写小说,不管未来会写什么,写作总是一条不能斩断的路,林清玄会一步步往下走去。
7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,8岁,获得了全台湾儿童绘画赛优选,10岁就开始读小说,林清玄记得小时最喜欢的是《西游记》,喜欢里面的天马行空。
1972年,考取世界新专电影技术科,在学时非常活跃,开始认真写稿,而绘事则暂时抛开了。在世新的时候,创办过《电影学报》,担任《奔流杂志》编辑,在《新闻人》周报任总主笔。这段时候,在文坛渐露头角,开始受到了瞩目。
写报导
这些年,林清玄写报导写得多,写散文反倒写得少了,不过,他并不觉得可惜,虽然他自己也了解,报导到底只是报导,不会成为文学的重镇,甚且有一天它会式微。不过,林清玄自觉还年轻,这段时日,就利用报导来磨练自己的事,创作的`事,稍候也不迟。
林清玄也自认,还未到定下一个风格,一个走向的时候,他还是要去做多方的揣摩,去走多样的路,去写多样的文章。而且他还会去角逐其他以篇对篇,或是一堆对一堆的奖目。因为,他一直是永恒的新人,一个新人永远都需要去竞逐,永远都需要接受新的肯定。
散文创作
林清玄的散文创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,第1个阶段是在70年代他初登文坛的七八年间,散文集有《莲花开落》《冷月钟笛》等;第2个阶段是他从1980年结集《温一壶月光下酒》起,相继出版了《白雪少年》《鸳鸯香炉》《迷路的云》《金色印象》《玫瑰海岸》等;80年代后期迄今,是林清玄散文写作最辛苦和最多产量的第3阶段,在这个阶段里他以10本“菩提系列”震撼了文学界内外。林清玄也是大陆读者广为熟知和爱戴的畅销书作家。应广大读者要求,又以真诚之心,感性之笔,将多年来感悟的智慧精华,结晶于《玄想》、《清欢》、《林泉》三册书中。首次公开这些年来的写作心得,使人格外珍惜和感动。
成就荣誉
1973年开始创作散文。他的散文文笔流畅清新,表现了醇厚、浪漫的情感,在平易中有着感人的力量。作品有散文集《莲花开落》《冷月钟笛》《温一壶月光下酒》《鸳鸯香炉》《金色印象》《白雪少年》《桃花心木》(选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第3课)《在梦的远方》《在云上》《心田上的百合花》《菠萝蜜》《用岁月在莲上写诗》等。其《和时间赛跑》被选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课标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13课,也是北师大版四年级下期第十一单元第2课,《百合花开》还选入冀教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第12课。并且他的散文集一年中重印超过20次。《桃花心木》被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3课。
天心读后感悟篇二
刚升初中的时候,学校离家蛮远的,再加上还要上晚自习,每天到家都要九点多钟。那个时候,早已是众多人家休息的时间了。父亲为了锻炼我走夜路,晚上不再接我。放学之后,一个人要走很远回家,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来说,难免会胆战心惊。但是有月亮的时候,心就会像林清玄说的那样慢慢地沉淀下来,对夜的恐惧也不复存在。
《月在天心》是一篇很贴近我们生活的文章,就像里面写的`:“更好的是,在月光底下,我们也觉得自己心里有月亮。有着光明,那光明虽不如阳光温暖,却是清凉的,从头顶到脚尖的指甲都感受月的清凉。”
可不是吗,月光是亲切而又有着微微凉意的。尤其是在夏天酷热的白天之后,月光总是会让人感到那清新的凉意。经过一天的学习。走在独行的路上,望望月亮,顿觉驱走了那烦躁的思绪,连心底都是一片让人舒畅的清明。
夜里的月光是很亮的,尤其是没有云朵的晚上。偌大的夜空挂着一轮玉盘似的圆月,月下的景物清清楚楚的显现出来,纯粹的让人想到膜拜。但是当你仔细一找,却发现不知要拜向何处。就如同那文章说的:“那不像是太阳的投影是从外面来的,那片光明犹如从草树,从街路,从花叶,及至从屋檐下,墙垣内微微地渗出,有时候会误以为万事的本身自在的光明。”
也许你会有了疑问,在我们行走的时候,月也在动,这究竟是真还是假: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,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月。它独一无二,就如同你本身的独一无二。当月亮照耀我们的时候,它们是发着光。心灵之月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处住所,如何让它长久的发光,关键在于你是否知道它的存在。作者说:“只有极少数的人,在最黑暗的时刻,仍散发着月的光明,那就是知觉到自己是月亮的人。”
回归自己,让自己心中的月发光吧!
天心读后感悟篇三
很早就有耳闻林清玄这位台湾的高产作家的作品很有禅意。偶然在一些杂志上看到一两篇,觉得也确是很好。最近借着选修课的契机,借得一两本散文集来看,阅毕,有些许感想。
林清玄作品大多短小,却能在生活不经意的小事小节中,悟出人生的道理,读来倍觉亲切。其文字虽不华丽,但简单朴素中也能把人生道理娓娓道来,说得入情入理,无名的感动、温暖总在文末处涌动。又名林大悲的他,佛理常常成为他说理的方式,读来因而倍觉空灵。读其文,确是一种心灵的洗涤。
在《沉水香》一文中,他说:“沉香最动人的部分,是它的‘沉’,有沉静内敛的品质;也在它的‘香’,一旦成就,永不散失……浮世是水,俗木随欲望水波流荡,无所定止。沉香是定石,在水中一样沉静,一样的香。一个人内心如果有了沉香,便能不畏浮世”。若是平常,在尘世中迷茫不知所措的我,断不能静下心来,想到这样的哲理。要怎样的人生品质,要怎样的处事方式,确是需要斟酌,一天天成长。“生命的意义就是使自己每一天都有一些心灵与智慧的增长,每一天都对世界有一些奉献与利益(《生命的意义》)”
秋天了,是丰收的季节,也是悲秋的季节。看着天气一天天变冷,树叶落了一地,世界渐渐由春夏的热闹变成秋冬的萧瑟、冷清。不免伤怀:美丽的事物都不长久。年华易逝,青春易老。偶有读到“一切因缘的雪融冰消或者抽芽开花都是自然的,我们尽一切的也无法阻止一朵花的凋零。因此,开花时看花开,凋零时就欣赏花的凋零吧”(《凋零之美》)“不论年华去也、不论分合聚散、不论多少的背弃与分离,每一年的春风总是在的。人面可能分离,桃花必会凋谢,只要我们在分离与凋谢中不是去微笑的心,就能永远与春风相约”(《笑春风》)。诚然如此!
的11月11日,爱情,或者说脱离单身是最热门的话题。许多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寻找所谓的真爱,化妆晚会、相亲会等等形式层出不穷。身为局外的人,面对着一出出的好戏,我不禁生出疑问:这样的方式意义有多大?爱的到底是外在的金钱、外貌、地位,还是真的内在?正如《百合》中所说的:“这世界,爱百合的人很多,能珍惜那纯净、优美、芬芳的品质的人很稀有……口里说出相爱的话语何其容易,心里真正相知与疼惜是多么艰难!”希望有一天,这世界能够不那么浮躁,可以安静地、文明而有序地、温暖地转动着。那么,我们可以说。爱情很简单,相爱很容易。
人生,总是在欲望中纠结,有的人可以把欲望看的云淡风轻,因而过得怡然自得,健康长寿。而有的人却深陷欲望的泥沼,不能自拔。每天的新闻,某某人为财而亡,某某人为色锒铛入狱。看得人惊心动魄,唏嘘不已。其实“物欲的追求与心灵的追求乃是天平的两端,一个有慧心的人自然可以找到既可以充饥又好吃的面包”(《生命的馅》)
掩卷长思,人生的许许多多的智慧,需要历练才能真正体会。书本所能给的,是一些启发与思考,要化为已有,需要更多的体验。
天心读后感悟篇四
林清玄简介:林清玄,1953年出生,笔名:秦情、林漓、林大悲、林晚啼、侠安、晴轩、远亭等。台湾高雄人,当代著名作家、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。1953年生于中国台湾省高雄旗山。毕业于中国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。曾任台湾《中国时报》海外版记者、《工商时报》经济记者、《时报杂志》主编等职。他是台湾作家中最高产的一位,也是获得各类文学奖最多的一位,也被誉为“当代散文八大作家”之一。
《煮雪》读后感:
《煮雪》从一个极度浪漫的传说开始——住在北极的`人因为天寒地冻,张嘴说话都能结成冰,听的人只能把结成的冰带回家慢慢烤来听……若是我听了这个故事,大概也就一笑了之,林清玄却不然,他借此传说展开了丰富的想像,进而通过“浪漫”这个词联系到爱情。
爱情,离我们这些学生应该是遥远的,不可触及的,但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,心中总有暗流涌动。
在这里,我先暂且称其为“语雪”吧。
当然,这也有不方便的地方——倘若是问路呢?我要是生在北方,可得为这件事费一番心思;抑或是有急事呢?那定要升起一把熊熊烈火吧?事物的一切就是这样都有两面性的吧!
天心读后感悟篇五
凡属美者,
不仅经常为美,
且为其自身而美。
如果人生值得活,
那只是为了注视美。
——柏拉图
白孔雀开屏了
到台湾故宫博物院看画,心里还记着宋徽宗的《腊梅山禽图》,宋徽宗在画里用美丽飘逸的瘦金体题着淡淡的诗句:
山禽矜逸态,梅粉弄轻柔。
已有丹青约,千秋指白头。
说他愿意一辈子醉心于画画,也不愿意做皇帝,皇帝是白头的工作;而艺术是千秋的志业呀!
走在至善园安静的小径上,突然,有一个陌生的小男孩沿着小径奔走,逢人就说:
“白孔雀开屏了!”
“白孔雀开屏了!”小男孩一路叫,一路笑,沿路与人分享他发现的喜悦。
识与不识的人,听见这个消息,都随他往至善园角落的鸟园走去。
我随着小男孩走到鸟园,果然看见了白孔雀美丽而惊人的开屏。令我更为惊奇的是,不只一只白孔雀开屏,而是两只白孔雀同时开屏,还有另一只硕大的蓝孔雀也开屏了。
三只孔雀在不算宽敞的鸟园中,一起张开了动人的尾羽,闪着光芒的尾扇在园中抖动,更使人感觉到春日的喧哗与春情的萌动,但旁边的几只母孔雀不为所动,静静地、埋着头吃着槽中的饲料。
白孔雀与蓝孔雀的开屏,有着惊人的美,使我敛容肃立,心里突然浮起一个念头:“是园中的孔雀为美?或是画里的花鸟为美?自然中美的实质或艺术中美的实质是一致的吗?自然美与艺术美是不是同一个品质?”
去眉眼盈盈的地方
这使我一边欣赏孔雀,一边深思。
一个无法在自然中探触到美的人,是否能具备艺术欣赏的眼光呢?
一个对生活之美无感的人,能不能在创作中找到美呢?
一个人可不可能欣赏孔雀开屏又吃孔雀肉呢?
一个人能不能一边写诗作画,一边焚琴煮鹤呢?
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都是否定的,因为生活之美、创作之美、自然之美、艺术之美都不是独存的,而是同一品质的。
先是看见了孔雀的、花鸟的美:
好鸟枝头亦朋友,落花水面皆文章。
再看见了草坡上的野草与昆虫皆美:
除之不尽,爱之可也。
接着看见了怪石与荆棘,各有各的情境:
花若解语还多事,石不能言最可人。
抬头远望群山,低眉俯看流水,一静一动,一刚一柔,一猛一媚,一仁一智,正是人生之美的飞梭,织成一片锦绣。
水是眼波横,
山是眉峰聚,
拟问行人去那边,
眉眼盈盈处。
我要去眉眼盈盈的地方,去看那美丽的山水,山水正以眉眼和我对语呢!
这世界上并没有必美之地,文学艺术家因此要锻炼看到什么都能映现出美丽的心影,打开心眼去看见美的境界,并不断去追寻更高远之境。
美,是同一品质
我喜欢钱穆先生说过的一个故事。钱穆青年时代有一天路过山西的`一座古庙,看到一位老道士正在清除庭院中的一棵枯死的古柏。
钱穆好奇地问:“这古柏虽死,姿势还强健,为什么要挖掉呢?”
老道士说:“要补种别的树!”
“补种一棵什么树呢?”
“夹竹桃。”
“为什么不种松柏,要种夹竹桃呢?”
老道士说:“松柏树长大,我看不到,夹竹桃明年就开花,我还看得到。”
钱穆先生听了,大为感叹,他说:“‘士不可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’丛林的开山祖师,有种夹竹桃的吗?”
钱先生常以此勉励门人,做学问的人不要只种桃种李种春风,还应该种松种柏种永恒。
文学家、艺术家不只是学问家,心地高远能望见松柏,却也能欣赏夹竹桃开花的美丽。
美,是同一品质。
智巧兼优,心手双畅
一个完全不认识字的人,也能贴近那种刚健与婀娜;正如一个第一次张开眼睛的人,会被河山的壮阔与柔媚感动。
我特别喜欢唐代的书家孙过庭的《书谱序》,里面写书法的文字曾使我吟诵再三:
观夫悬针垂露之异,奔雷坠石之奇,
鸿飞兽骇之资,鸾舞蛇惊之态,
绝岸颓峰之势,临危据搞之形,
或重若奔云;或轻如蝉翼,
导之则泉注,顿之则山安。
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,
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,
同自然之妙有,非力运之能成。
信可谓智巧兼优,心手双畅,
翰不虚动,下必有由,
一画之间,受起伏于峰杪,
一点之内,殊衄挫于豪芒。
天呀,这是多么美丽的文字!我在故宫的展览室绕室三叹!
平面的书法,一下子悬针垂露,一会儿奔雷坠石;大鸿与鸾凤飞舞,野兽与蛇蝎惊骇;站在最危险的高峰绝壁边上,有时重得像奔跑的云,有时轻得像蝉的翅翼;舒展的时候如泉水注流,顿挫的时候安顿如山;纤细时像初升的月亮跳出山崖,潇洒时又像众星列在星空;这种与自然相应的妙有,不是光靠力量运作就能成就。
永远抒情的心
我喜欢这书帖,是看到了艺术与自然之间的紧密相连,文字与艺术的窍门不就在这里吗?
像是一只开屏的白孔雀,突然展翅,飞入了画图之中。
也像是一只图画中的竹鸠,突然飞到我们的眼前歌唱。
我在册页中读到的美,在自然中,我也见及。
我在卷轴里发现的情意,在生活里,我也体会。
我看一笔的乾坤,也看万象的神奇。
我观一画的盎然,也观万物的生意。
文学家的心是无碍的,他出出入入,入而体会白孔雀之心,出而看见白孔雀的美。
在某些特别神秘的时候,我们象形、转注、假借、会意,把心境凝注于纸,那一刻,就像白孔雀开屏。
在我们生活的四周,充满了美好,也充满了情意;在我们生命的历程,充满了生生之机,也充满了洋洋之趣;那是因为敏锐的品味使一切普通的都变为美,进而使心性变得神奇、浪漫、古典。我的文学、我的创作,正是根源于这敏锐的品味。
近年来,我随手写下创作的感想,先后完成了《玄想》、《清欢》,现在把这本书定名为“林泉”,对我而言,创作正如林间涌泉,是天然的,可以无量涌出;是清澈的,可以无限畅饮。
我相信、现在乃至未来,文学家可以书写都会、机械、电子、科幻,以及人性的灰黯和纠葛,但在我的心灵深处,永远有一道清泉在密林中涌出。我始终相信,文学的终极是在走向道、走向自然、走向真情与挚爱,走向一个更超越而高远的世界。
文学,是温柔的心,浪漫的美,完满的感性,永远的抒情……
林清玄
二00四年夏日阳明山下清淳斋